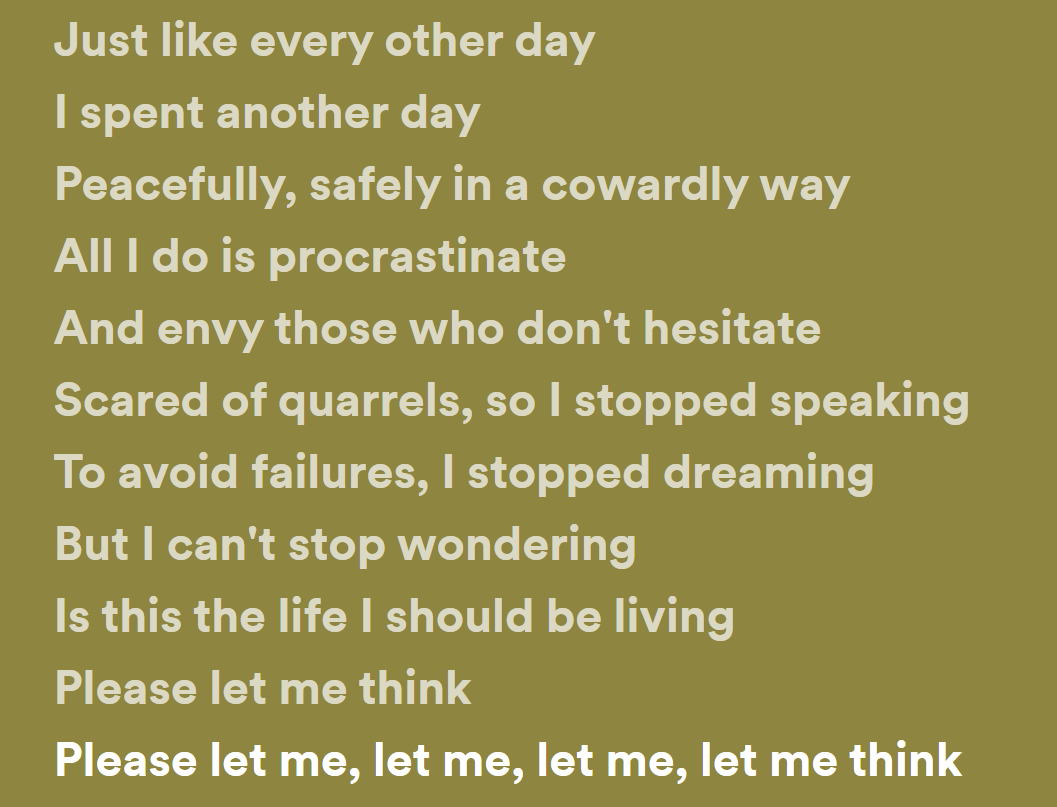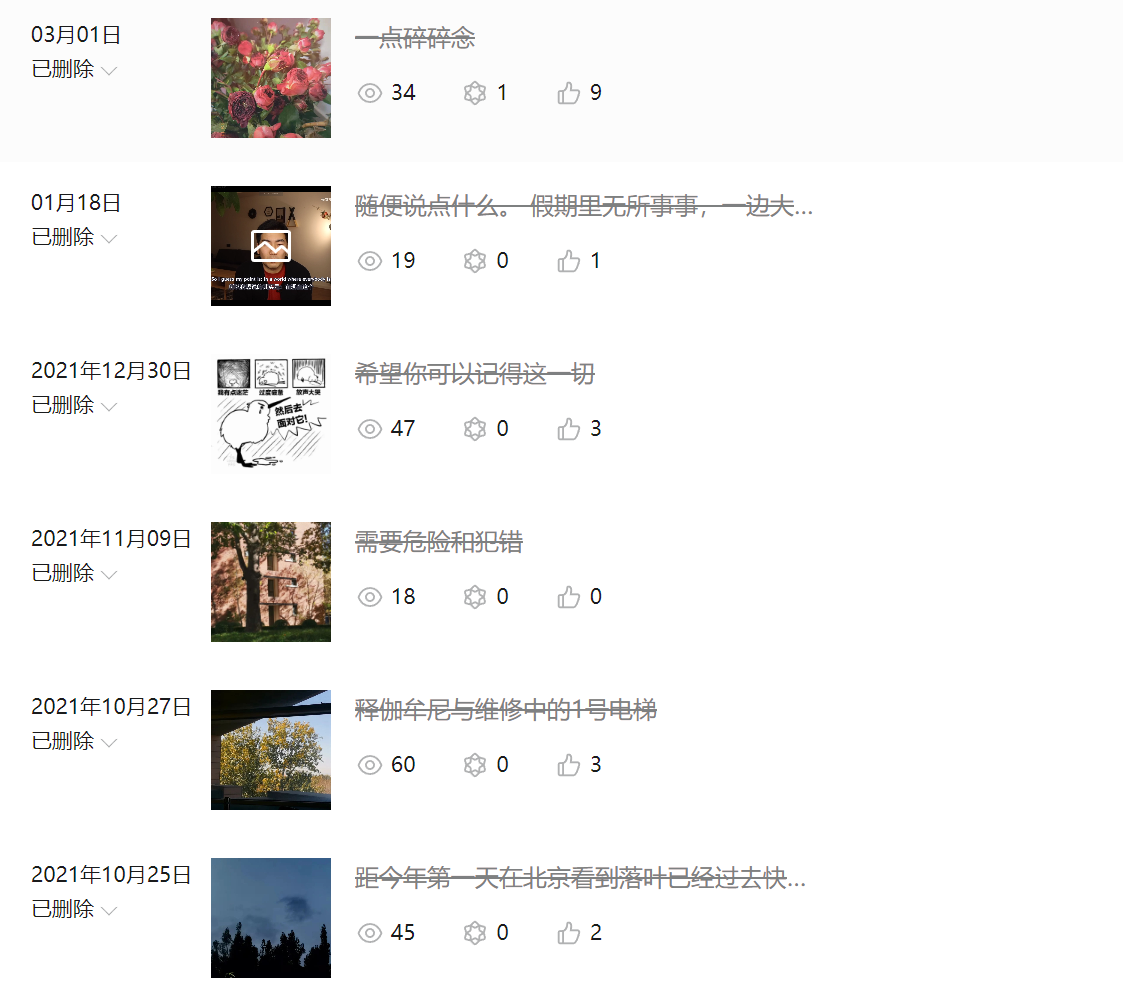只管去写“
0 我也不知道会写什么
今天是2022年12月8日,早晨九点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起床过,已经记不清从哪一天开始就放弃了早起,睡梦是香甜的,是人活在世上唯一的念想。但今天,或许是因为没有关灯,或许是因为感染后呼吸不畅,也或许是因为心里为开题答辩惴惴不安中,也或许是出于愧疚,或许混杂着以上所有再夹杂着很多我说不清的情绪,总之是这样起床了。但我仍然没有办法适应光亮,犹豫再三,像已经蛀牙但仍然偷吃糖的小孩一样去关掉顶灯——在我看到的所有教你如何保持积极健康状态的文章里,都会提到说要阳光要晒太阳,身体在黑暗的环境里会减缓思考速度。但真的很抱歉,我真的在黑暗的房间里才更自在。
或许还是应该更遵从内心的选择,相信你自己的感受,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。布迪厄讲,社会行动者积极主动地决定那个决定他们的情境,只有社会行动者决定自身时,他才是被决定的。潜在的可能性便是,行动者可以积极地变更那个决定的情境,如果在这套体系里活得不好,我们可以换个体系继续生活。生活的希望感就在这里生发出来。最近时常会觉得活不下去,因为在此地看不到希望,既看不到自己的希望,也看不到这片土地的希望,最后会觉得人类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,整天跑来跑去吵来吵去究竟有什么意义。短暂获救的办法是进入“可掌控感”的幻象里,我一向认为人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,太多未知的因素摇摆着一切,但还有一点事情是自我可以做的。昨天跟洞友说起上个冬天见面,看流星喝热红酒,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,我看着相册里跨年夜的合影,记忆鲜活得也仿佛昨日。我兴奋地决定,在今年跨年跟洞友一块做第一期播客。我说我想做播客已经说了太久,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什么东西来,但在群里宣布跨年是第一期之后,我的脑海中仿佛已经看到了我的show notes 页面。
一直以来,我的恐慌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担心自己长成父母那样的人——或许这是每个东亚儿女的诅咒和梦魇,永远在担忧自己是不是变成自己所深恶痛绝的那一面。对我而言,我的恐慌叫作成为姐姐,成为那个永远顺着社会节律走的“美满”,成为那个永远逃不掉的“稳定”。但或许不必太害怕,因为我仍在担忧,我就不会成为那样的人,因为我仍在写东西,并且希望继续写东西,所以期望仍在延续。最近在毛象宇宙里获得了一些力量,虎鲸已经是一名快40岁的女性,但仍在鱿戏,在写小说,在做游戏,在分布式网络用小黑猫表情包跟网友聊天,非常inspiring。还有仍在画漫画的luran,区别可能在于虎鲸选择不婚而luran已有子女。但总之都是“有趣成年人”的可靠范本。